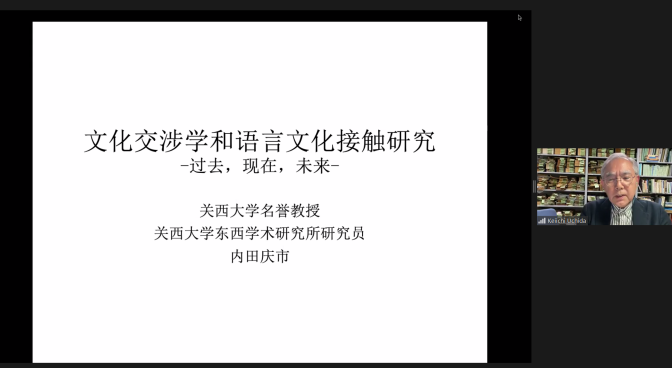
内田庆市(Uchida Keiichi)日本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中国近世语学会会长,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副会长
首先,什么是文化交涉学?我们关西大学2007年开始提倡转到新的学科叫做文化交涉学,英文叫作“Cultural Interaction”,它一般翻译成“文化交流”,但是我们特别叫文化交涉,为什么?以往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积累了针对个别专门领域的文物或者制度所进行的系列研究,所以缺乏与其他学问领域的接触,而失去了研究的总体性。我们所开创的文化交涉学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突破了以往以国家或者民族为分析单位,而设定东亚这样一个具有某种统合性质的文化综合体,关注其内部所发生的有关文化的形成、传播、接触以及变迁现象,从综合性的立场出发以多元化的视角对文化交涉的总体形态进行阐释,这样的学问叫作文化交涉学。我们的关键词是跨领域、跨文化。我们的研究领域包括很多领域——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哲学、美术等等。还有我们主张跨地域,中国、朝鲜、越南、欧洲等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多对多,这跟文化交流不一样的。还有多元化的视角,我们很重视从周边看中心特别是域外文化交涉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我的研究方向是汉语语言学和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特别是西洋人怎样研究汉语的。我首先就这方面来说,汉语语言学的日本和中国的对域外资料的看法不一样,日本早就已经开始这样的研究,50年代已经开始注目这些资料的重要性。如太田辰夫先生、香坂顺一树荫和尾崎实等,还有今人的古屋昭弘先生,大概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到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的三种语体的问题。中国国内怎样?中国当然有罗常培这一类人,他1930年已经发表过“耶稣会士在音韵史上的贡献”,但是后来没有罗常培之类的人,只有80年代末出现复旦大学的周振鹤老师,还有钱乃荣、游如杰等“海派”学者。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以前叫做海外汉学中心的张西平、姚小平、李雪涛等。我们当时1997年开始有近代东西语言接触的国际研讨会的,最早我们开始的是1997年,在上海社科院开了一个研讨会,题为“近代学术英语的形成和变迁国际研讨会”,还有北外开了一个“西学东渐和语言交流国际研讨会”,后来慢慢增加了。我们2000年跟沈国威一起组织了一个学会叫做“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会”有这样的学会,我们发行了《或问》学术杂志,后来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2004年开始的。现在北外历史学院里面有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中心,现在比方说张美兰老师、厦大的李无未老师、北外的王继红老师,他们都能够来搞这个方面的研究的。
域汉资料对于汉语研究的重要性在哪里的问题?我今天拿语法论来讲,刚才好像马西尼先生已经说过,马氏文通以前的汉语研究的特点是这样的:只有小学就是经学的附庸,只要经学的注释或者训诂学,只有这样的人搞研究的,特别是以虚词或者助词的研究为主。当然1840年左右有一个中国人叫做毕华珍,有这样的人,他写过一本书《衍绪草堂笔记》,这本书以及他提到汉语语法的内容。西洋的艾约瑟他也提到《衍绪草堂笔记》的先驱性,但是很小的例子。但是西洋人的汉语言研究怎么样?刚才马西尼先生已经说过的,比方说《漳州话语法书》于1620年左右出现的,还有卫匡国的Grammatica Sinica,还有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还有巴耶、马勒瑟、傅尔蒙这一类的有很多。19世纪以后,首先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卫匡国的《中国文法》的内容,他当然按照印欧语的框架来描写汉语语法的,所以把介词(前置词)和方位词混同,但是他已经注意到汉语的个别特点,如一词多类、汉语量词的问题,他们已经提到过的。他的汉语,当时的南方话为主的,所以他的汉语里头有很多南方话的特点,比方说“抓得紧”“xx得紧”,有这样的词汇出现的。后来比如说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最大的特点是把汉语的语体分成三种:第一种高雅的,第二种就是高雅和粗俗中间的位置,第三种粗俗的语体。另外换句话说,第一种是文言的,第二种半文半白的,第三种是白话,有这样的三种的语体大家已经提到过的。后来19世纪以后的新教传教士为中心的传教士,他们汉语研究很多,如马士曼、马礼逊之后有很多 ,如江沙维、艾约瑟,雷慕沙不是传教士,还有萨默斯、罗存德、高第丕等,有很多这样的著作,还有他们出版了很多的课本,比方说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还有狄考文、戴遂良等。特别是威妥玛的语法论我们要注意的,关于《语言自迩集》的研究一般来说从北京官话的或者词汇和教学法的方面的研究很多,但是从语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得,除了宋桔的《〈语言自迩集〉的汉语语法研究》以外,很少的,但是应该重视。因为他的语法论,比方说句子分类等,我们看到他已经把汉语的句子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跟现代的汉语语法的系统一样的。还有他的量词的看法也是很特色的。他这样说的:“量词,话里凡有提起是人是物,可以有上头加一个同类的名目,是要看形象的用处,作为陪伴的字。”所以威妥玛不叫它量词,叫作“陪伴的字”。但是这里值得注目的是他已经注意到量词的功能,以前俄国的汉学家龙果夫、日本的汉学家大河内先生说的“个体化”的功能。量词的“个体化”是specific或者particular和generic的对比,也就按照功能他已经注意到的。
还有《语言自迩集》的传播和普及也很有意思的,《语言自迩集》给日本的影响很大的,在日本最早的汉语课本就是威妥玛的这本书。以前这边有很多抄写的东西。后来他们出版了《亚细亚言语集》,按照《语言自迩集》来编辑出版的,日本最早的北京话的课本,可以这样说的。但是《语言自迩集》除了日本以外,还有中国国内、法国也有,比方说法语版的《语言自迩集》1879年的,这样的东西也有的。法语版是土山湾孤儿院的郁炳蔚编的,法国的传教士他编的东西,这个很有意思的。比如线装本在中国国内,比方说上海的复旦大学或者学家会图书馆收藏。但是为了中国人学官话的在课本上用的是《语言问答》,我最早在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后来这本书在罗马的国内图书馆也有收藏。但是后来发现,在复旦大学里面也有很多《语言问答》,《语言问答》的内容不是《语言自迩集》的,但是《语言问答》这本书是按照《汉族文法问答录》来抄写的。还有中国国内还有《语言自迩集》,语音本也有的,所以《语言自迩集》除了欧洲人学汉语以外,中国人也用过,还有日本人都用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很有意思的。
西洋人的汉语研究的优点在哪里?我经常能够提到过的有四点:一个西方早已经确立了语言学或者系统性的语法学;还有他们是外国人,所以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和汉语的对照的方法来客观地描写汉语的现象;还有第三,他们用罗马字来标音,中国传统的“反切”法,有这样的标音法的,但是“反切”法跟罗马字来比较的话,肯定是罗马字标音肯定更科学的是吧?第四,他们(传教士为主)的传教的范围很广泛的,所以他们已经注意到汉语有官话和方言这样的区别。所以这样的四点就是西洋人的汉语研究的优点,这些正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是采用“周边方法论”的主要意思。就按照语言接触或者多元资料有很多可能性的,比方说音韵学的研究,当然很有用的,因为给他们的资料都用罗马字来标音,所以当然对音韵学的研究很有有用的。还有官话研究,西洋人的官话研究很早就有的,比如说利玛窦他已经提到过,“中国除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他已经说过的。还有曾德昭也这样说,“中国今天只通用一种语言,即他们称呼的官话,也即曼达林语。”马礼逊或者《官话文典》,就是万济国他已经注意到了。应该注意中国人的发音方法,但不是哪个中国人都可以的。最好是南京省和其他地方的居民。万济国的时代普通话不是北京话的,这是南京省的官话,很标准的。这个地点结果已经能够知道了。还有后来M. de. Geiges他也提到过的,“中国只有两种口头语,是官话和乡谈,不管北京、广东或者其他城市,人们都用官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区别只在发音。发音较好的地方主要是江南地方。”后来罗伯聃(Robert Thom)也说过,所以这样的看法当时的中国人没有的,这样的资料对官话的研究也很有好处的、还有方言的研究,还有语体论的问题,语体论的问题,特别是汉语《圣经》来说的话,比方说用文言翻译圣经的也有的,但是白话的、北京官话的《圣经》也有的,但是半文半白的也有的。所以他们把半文半白叫作“浅文理”。对于我们研究汉语的语体的时候,这样的资料很有用的。还有东亚的英语学习史研究,也有这样的研究可以。还有英华字典的谱系,这个刚才马西尼先生已经说过的,他们先有葡汉、汉葡,还有汉拉、拉汉,各种对照字典,后来《华英》字典出现的,所以英华字典的谱系,还有汉外对照字典的研究,这个很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洋泾浜英语,或者广东番禺或者汉儿言语、拟蒙汉语等。一个语音节奏发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Pidgin,这样的研究也可以做的。还有当然近代的译词和概念史的研究,还有翻译论的研究等等。所以我们建的语音接触、建的西学东渐来出现的,觉得那个东西有各种可能性。汉语圣经,这个也很有意思的。这是麦都思的《新约全书》,主要是南京官话来写的,但是北京官话的也有,还有这样的。欧文资料以外的域外汉语资料也很有意思的,比方说朝鲜的资料,比如元代的《老乞大》《朴通事》等等,这样的汉语课本很有意思。还有满蒙汉资料,如《三合语录》《清文指要》,这样东西很有意思。还有琉球官话,琉球人很早就去北京,所以他们也学过汉语官话的,他们编的这样的资料《学官话》《百姓官话》;还有唐话资料。还有日本人编的汉语课本,这个很有意思了,这个应该要注意的;还有越南的资料等,所以有各种资料,这样的东西都能够对汉语的研究很有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