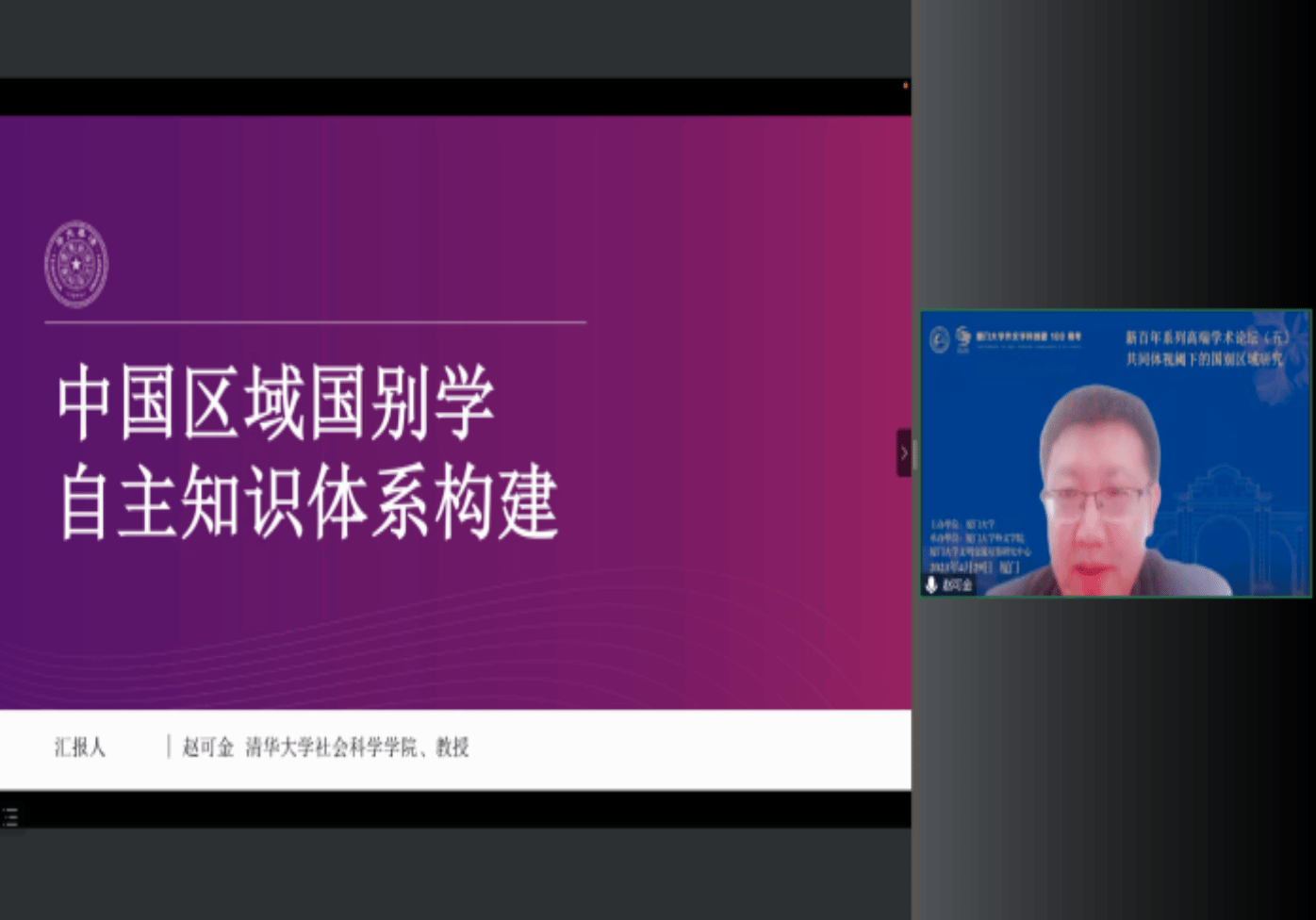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体系构建》,为什么讲这个题目?一个方面是去年4月2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的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只是区域国别区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学科,哲学、社会科学都面临着这个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问题,国别学作为一个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它能否构建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对于学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在历史上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思想的崛起,或者说是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思想的崛起大国的崛起往往都会陷入昙花一现。中国的崛起很可能首先是经济的崛起,然后是军事的崛起,最后才是思想真正崛起。在这个三部曲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思想的崛起。
历史上像蒙古草原帝国、帖木尔帝国,这些帝国之所以能够横扫世界,是靠他们锐不可当的军事实力,但之所以在一夜之间就会土崩瓦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非常不成熟,所以他们在征服了文明之后都会被文明所反征服。所以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崛起,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在考虑这个区域国别学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争论,因为它是很多学科。从现有的目录来看,它是历史学、语言学和法学、理论经济学四个学科。但事实上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可能不止于这四个学科,而且这四个学科也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区域国别学。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一门学科的成长实际上是近代的产物。我们今天大家在争论区域国别学到底以哪个学科为主,像我们厦大就是外国语学院是吧?还有的是强调政治学、有的强调历史学,好像理论经济学和和其他的法学学科。实际上这里面之所以大家来争这个,主要是学科地位所决定的。我们在政治学里面主要是从事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在推动这个事情。在外国语言文学里面,主要是非通用语种在争夺这个东西。历史学比较超脱,从建学科的过程来看,政治学和外国语言文学总体上这两个学科是不愿意来推动区域国别学一级交叉学科的建设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新建一个学科就意味着分兵,把现有的学科规模减小,有一部分力量就会分流到区域国别去另立山头,那么在资源分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历史学和法学(其他的法学法律)他们相对比较超脱一点,觉得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区域国别学建设,我觉得不能够放在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就是从奥古斯特·孔德以来,社会科学的学科化的这样一个框架当中。
应该往前追溯,往前追溯人类文明发源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一种知识的追求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刚才秦亚青老师从共同体的角度,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我是从文明的角度,其实文明也是一种共同体,如果从文明的角度去追溯的话,我们来看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可能仍然生活在轴心时代的这个空间里面。在轴心时代之前,宇宙变化、冰河时代过去,然后人类文明诞生。在漫长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世界各地没有什么差异的,人类在共同地遵循着自然的规律。人类之所以有差异,还是轴心时代以来的事情,大约是从公元前500年或者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500年,轴心时代这个过程是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它在发展当中由于受到了不同的地理气候特征的影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精神的关系这三大问题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和路径,所以导致文明发生了分化。一种文明向西走了,一种文明向东走了,这两种文明到今天沿着自己的逻辑在向前走。当然近代以后,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撕开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缺口,导致它在世界范围内再进行纵横驰骋。我们似乎生活在这种整个笼罩在西方文明的框架内,甚至在区域国别学的构建当中也经历了欧洲主导的东方主义阶段和美国、苏联主导的区域学或者是区域研究的阶段。实际上无论是东方主义还是区域学都只是这个区域国别学构建的一个知识体系。
我们中国的崛起作为代表东方——中国、印度,包括伊斯兰世界,我们代表东方实际上还有另外基于元初文明、轴心时代文明的这种基因,是由另一个知识体系,而这两个知识体系恰恰能够共同来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所以知识本身是人的一种生命力。北京大学的张岱年先生讲,“知是一种相遇和接触,识则是一种识别和区别。”我们接触到了什么?然后从中识别出什么样的东西来,这构成了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历史上每天都在接触新的东西,导致我们的差异的关键是我们识别的时候我们的视角和方法不同,知识是在开放自由的空间内释放自己能量的产物,是一个体系,它涵盖了人在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从三个问题的回答的不同的角度,轴心时代出现大致来看,我觉得出现了两种文明形态:所谓轴心的文明,一种是以圣经、耶稣基督为代表的这种有神论。有神论认为人的精神是来自于上帝的,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去获得同上帝、验证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而佛经它强调是无神论,认为智慧是来自于人自身的觉悟,认为修行还是获得觉悟唯一的渠道,只不过修行的方法有顿悟、有渐悟。我们今天在分析人工智能的时候发现仍然是佛经和圣经两种智慧的逻辑在起作用。从圣经的智慧来讲,它说量子纠缠,所以人工智能是去中心化的、是自组织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近代以来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种市场,到了市场的供求供需,到了量子空间里变成一个人工智能的自组织。而在佛经里面,它强调的是超越色空、泯灭二边,它是一个强调再中心化的量子计算,这两种实际上代表着两种逻辑,今天我们仍然无法摆脱这个轴心时代,也就注定了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无论是哪一个学科都可能存在着认识这个世界的不同路径,由此导致我们看轴心时代是点燃了人类文明的第一把火,这一把火在西方终结于黑格尔,我们说黑格尔终结了德国的西方古典哲学;在东方终结有王阳明,王阳明也可以说终结了中国的古典哲学。你看他们两个无论从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行动论,都是和佛经、圣经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这种分化一直持续到今天,也就是形构我们今天所谓东方和西方这种认识的边界。所以从三大问题的回答来看,在上述两种智慧力量的推动下,我们的知识体系它是存在着文明基础,大致的我觉得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侧重于解决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神关系的地中海文明,地中海文明它是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共同哺育的产物。我们看两栖文化,它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就是我们今天西方知识体系的一个基础。所谓的文艺复兴,复兴的是古希腊的精神和古罗马的美德。古希腊崇拜的是知识分子,所以古希腊人爱智慧,哲学非常放大,而古罗马崇拜的是农夫和武士,比较重实用、还重忠诚。这两盏探照灯等于说为西方是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而中华文明,我们重在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是从周公的周礼体系,还是到后来的儒释道,始终关注的是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所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中国的文化解决的是从生到死的问题,生前和死后的事情中国文化是不管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东南亚以后,东南亚的世俗生活基本受中华文明影响,但是东南亚在精神上并没有受到中华文化太大的影响,而是受到了印度的影响,无论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是婆罗门,都塑造了东南亚的内心世界。我们跟东南亚人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内心的区别,不是外表的区别,包括我们跟印度的区别,印度看重的是人和精神的关系,这个可以从早期的吠陀时代到奥义书,《墨客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是比较重视信仰的超验知识。它看重的是超验领域当中的知识。而中国看重的是经验主义的知识,所以这三种文明的基础,这三种文明实际上我们在影响西方的时候,中华文明虽然在世界各地都有汉学,但是影响的都是在世俗领域当中。我们的世俗伦理对西方有些影响,但是在精神世界都是印度文明影响的。所以连马克思都说我们的宗教来自于印度,所以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一个是重经验,一个是重超验。中华文明也有超验,但是它更注重人与自然和人与神的关系,所以这就奠定了西方文明在近代为什么能够掀开历史新的篇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从中国的知识体系来讲,中国是一个知识体系、是一个在早期就已经早熟了的知识体系。北京大学,还是北京大学梁漱溟先生讲中华文明是个早熟的文明。在古典时期,中国就有一种天下想象,强调经世致用,以伦理来建构社会,以文化来定义天下,构成了刚才亚青老师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或者是经验路径,到了近代之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我们才重新想象出国家这样一面旗帜,以救亡压倒了启蒙,以政党来建构国家,以革命来重构世界。当代我们现在所正在经历的,我们开启的人类想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以开放来融通世界,以创新来塑造未来。这是我们可以从几千年的历史时空看到中国知识体系实际上是一个“通三统”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着面临着大变局,要建设这个大学问,要成为大先生,实际上是也是有两个探照灯的:一个是服务国家的,要建立国家的知识体系;一个是服务世界、服务人类的,要构建人类的知识体系。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东西的,互为表里,对内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我们几千年中国知识体系发展的很简单的一个概括。如果详细来讲,我想前面两个部分我就简单得讲,第一个就是在古典时代,我们实际上是有,因为是形成了天下主义的知识体系。我们在四书五经,从早期的夷务和四方学形成的是一个华夷思维框架。我们通三统之后,我们的国学是经史子集、农医天算,通三统之后实现了从如墨道法到儒释道三教并立,然后最终剖破藩篱,实现儒释道三教圆融,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庞大体系。实际上是终结于唐朝的慧能和明朝的王阳明,慧能和王阳明实际上是互为一体的,只不过慧能出家了,王阳明没有出家。所以我们在古典时代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儒释道合一的体系。经历先后经历了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并和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对话,然后对世界产生了影响。近代我们受到了西方的启蒙,受到了西方的冲击,然后我们进入启蒙,启蒙之后,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师法欧美的西学、师法苏俄的马学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纳入了外国问题研究或者国际问题研究,形成了一个以从专业为主的知识体系向学科为主的知识体系的转变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看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从学科和专业当中,我们可以去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不同的象限里,不同的象限来看,到底哪一种最适合。所以我们在区域国别学构建的时候,可能也要考虑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哪个象限里,现在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我们怎么来构建一种看世界的手段、视角和知识体系,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区域过别学的知识体系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个是马学、一个是中学、一个是他学。马学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灵魂,这是我们近代以来所确立的一个指导思想;中学是我们的母体,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他学是区域国别学发展的重要的外部条件。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指向东方主义和区域研究那样,只陷入了他学,而是要把马学、中学和他学给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区域国际学构建知识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路径。构建成了之后,我们的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是包括三个部分,也就是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再一个是国际学,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研究;第三个就是全球学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整体的研究,所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在知识体系上应该是要把国别学、国际学和全球学结合起来。而国际国别学当中,每个国家都是一种文明,都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别学我们应该区别近代学和当代学,这是我们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时候,要特别把它进行适当的区分。国际学也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比较学,本国和其他国和研究的对象国之间做比较,可以比较政治、比较经济、比较社会、比较文化、比较各个方面;再一个就是关系学,国际学我们现在讲的国际关系学;第三个就是地区学,因为国家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同时在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都有它的地区的共同体或者地区的存在。所以我们要超越国家这个空间,还要把地区治理、地区化以及地区发展的逻辑纳入其中。作为全球学,我们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就要把我们的区域国别学,刚才贾文键老师提到的我觉得很有启发,比较的区域国别学,就与西学的区域国别学、与伊斯兰的区域国别学以及其他文明的区域国别学要进行对话,来思索和研究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全球学可能是我们未来区域国别学共同汇入的一个学科领域。国别学是它的过去,国际学是它的现在,未来可能就是全球学。
所以我们的未来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想这样的一个界定,就为我们指明了区域国别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即沿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和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建。沿着这个方向实现我们在开启新征程之后,新的通三统,实际上我们对人类思想的一种融合,超越国家、超越教派、超越族群,形成人类共同的知识。我想这是涓涓细流汇入大海,形成人类共同精神家园的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总得来讲,中国进入新时代,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求我们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同时中国的知识体系先后经历了古典的天下主义、近代的国家主义两种形态,在未来我们应该着力构建全球主义的自主知识体系,而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来自于先验哲学、经验科学和超验神学的三个知识源头的共同哺育,形成了国别学、国际学和全球学相应成辉的三个部分。我们应该把马学、中学和他学结合起来,走通三统的道路,确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建三大策略。通过这样我们逐步来发展和完善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系。自主知识体系虽然源于中国,在我们中国的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创造,但是它必将属于整个世界,它也会对其他的文明、其他的国家作出重要的思想贡献。